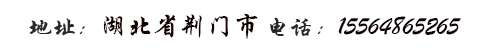关于北齐一朝ldquo汉rdquo
|
编者按:很久没有发文了,很是惭愧。于是把最近一篇很不成熟的一个初稿发出来当做最近的成果。本文尚未完成,甚至连结论也没有,这是因为我读的材料太少,心中的疑惑太多,不敢就此妄下断言。本文的话题是我很有兴趣的民族史方面的,不过我相关的知识与方法等于零,所以是一篇外行中的外行的文章,仅仅做了一些史料的梳理,没有任何创见,但我计划在未来很长时间内继续深入探究,不断完善此文,希望本文成为我深入一个话题的契机。 为非专业同学介绍一下本文的历史背景: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北族“汉化”成为潮流,不过留守在北方六镇的少数民族并未充分汉化,但在政权中被边缘化,还遭到了不少剥削。因而北魏末年,六镇鲜卑大起义,推翻了北魏,建立了东魏(后变为北齐)与西魏(后为北周)两个政权。这停止了快速“汉化”的潮流,“汉”不再受到尊重,反而有了贬低、诟詈之意。北齐正史《北齐书》中多次出现“汉”“汉儿”“汉人”之语,不过其含义与今天有不少差别。探究“汉”等词汇在北齐这样一个“胡化”政权中含义的嬗变,可以挖掘出更深刻的历史语境。同时,这也与后世乃至今日诸多语言习俗息息相关,我们经常使用“恶汉”“痴汉”“流浪汉”等辱骂性称呼,这个“汉”是怎么来的?本文即从这里开始。 关于北齐一朝“汉”字涵义与适用人群的几点问题 一、问题的产生 “汉”在今日有表示民族之意,不过并非自古如此。尽管早有“汉人”之称谓,但长期以来仅意指政权归属关系,作为民族意涵的“汉”直到大约南北朝时才频繁出现,其中尤以东魏、北齐朝为盛,前人对此已做了充分论述[1]。不过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北朝“汉”字作为民族的含义出现之后,其含义并非单一,“汉”“汉人”“汉儿”等词适用的人群也并非与今日的用法一致,甚至出现了诸多在今人看来深感矛盾的用法。“汉”的意涵与适用人群的复杂性,应当是以当时民族关系的变化,族类划分标准的多元性与模糊性为背景的。于是便有前辈学者从该问题的探讨出发,希冀一叶知秋,揭示北方当时剧烈的政治与文化上的变动。其中,笔者对陈寅恪、陈述、苏航三位学者的观点给予了主要关照[2]。 陈寅恪先生 陈述先生 三位学者的观点虽不能说完全相左,但侧重点全然不同。另外,笔者还发现,在引用同一则史料进行阐释时,三位学者的观点竟会出现迥异的说法,这引起了笔者的兴趣。按这一类史料,亦以北齐一朝最为集中。因此,以北齐一朝的相关史料为中心,对这些不同的观点做一番事实与逻辑上的考察,或可对这一问题收获更有见地的认识,起码证明此话题的复杂性。 二、史料辨析 1、源氏身世 《北齐书》卷五十《恩倖·高阿那肱传》载: 尚书郎中源师尝谘肱云:“龙见,当雩。”问师云:“何处龙见?作何物颜色?”师云:“此是龙星见,须雩祭,非是真龙见。”肱云:“汉儿强知星宿!”[3] 关于这则材料,陈述与陈寅恪文皆引《通鉴》胡三省注曰:“诸源本出于鲜卑秃发,高氏生于鲜卑,自命为鲜卑,未尝以为讳,鲜卑遂自谓贵种,率谓华人为汉儿,率侮诟之。诸源世仕魏朝,贵显习知典礼,遂有雩祭之请,冀以取重,乃以取诟。”[4]不过二位学者引胡说侧重点不一:陈寅恪重在“率谓华人为汉儿”,源师为南凉君主之后,《北齐书》尚载其父为今青海乐都人[5],按今日之说法为胡人无疑,却被鲜卑贵族称为“汉儿”。陈寅恪言:“此为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之教化为汉抑胡而定之确证。”陈寅恪之说,大抵得胡氏本意,姑且称之为“文化胡汉说”。而陈述则侧重“乃以取诟”几个字:既然二者都是鲜卑人,那么“汉儿”一定不是专指民族而另有含义,即诟詈之意,类似于“一个低贱的男人”。 苏航则同时挑战以上两种说法,在他看来,把这样的现象简单解释为不区分族群的诟詈之意很可能导致对某些时代背景的忽视;另一方面,陈寅恪所持的“文化胡汉说”也未得要领,真正让源师在高阿那肱眼里成为“汉儿”的,是他“代迁鲜卑”的政治身份。这种身份的人群,正是以高阿那肱为代表的六镇鲜卑在政治上严加提防的对象,因而会遭到其配之以“汉儿”身份而加以歧视[6]。 综合来看,笔者认为以上三种说法各有利弊。三者都看到了高阿那肱语气里对“汉儿”的贬低之意,这与六镇起义后北族汉化逆转,汉人地位下降的历史潮流一致。由此,陈述之说无根本性偏差。南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三云:“今人贱丈夫曰汉子,盖始于五胡乱华时。”[7]陆游这样追溯的证据是北齐文帝怒斥魏恺“何物汉子,与官不受”一句,似乎也讲得通。不过,北齐时的语境还是有些不一样:南宋人内部少有胡汉对立之事,“汉子”自然仅仅只是一个贬低的称谓;但在与源师、魏恺同时的不少记载中,“汉”依然有明显的民族区分之意[8]。如若将出现的带有贬义的“汉”字都解释为诟詈恐失之过简,也容易忽视这种贬低之意产生的过程与背景。 此外,陈述文一些细节的论述上亦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他引用《北齐书》卷二十四《杜弼传》中杜弼原话:“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并称身为汉人的杜弼不自称汉人,而说自己为“中国人”,可见“汉人”早已成为侮辱性称谓。此逻辑似乎并不可靠,当时南朝人亦称北方中原为“中国”[9],不足以见得杜弼是故意有所避讳。 而陈寅恪与苏航的观点在这则材料中都找不出逻辑错误,但二者之所以构成紧张关系,大概是因为说的过于绝对化。文化与政治,无非是当时不同人群构建族群认同的两种因素,说哪一种是决然支配一定不妥。试想若当时北族在每次给某类人群赋予“汉”的歧视性身份时都有一个清晰的指标来判定,又何以后代的“汉”成为一种不区分种群的诟詈之词。其间“汉”字的含义大约经历了一种从有明确族类边界到族类边界模糊再到干脆没有族类界限的歧视性称谓的过程。窃以为,北齐一代当处于转变的中间过程。 2、和士开之死 《北齐书》卷十二《琅琊王俨传》载琅琊王杀时任宰相和士开后,斛律光谓曰:“天子弟杀一汉,何所苦?”[10] 这则材料,陈述、苏航皆引用,阐释与上文无异。察《北齐书》卷五十《恩倖转·和士开传》虽载其为清都尹人(在今豫北冀南地区[11]),不过其先乃西域商胡,其父亦并非汉文化水平较高的士人。而史书中的和士开本人更是品行不端,除了不学无术、谄媚奸佞以外,还曾与太后通奸。尤其特别的是,和士开“又能弹胡琵琶”,大约其人有明显的西域胡人特征[12]。因此可以推断,无论和士开已迁居中原多久,时人是不会视其为文化意义上的汉族人的。 与此同时,笔者认为苏航将斛律光的话解释为政治集团分立的说法有些牵强。首先从文意上来看,斛律光之言将“一汉”与代表高贵身份的“天子弟”相对比,而非与代表文化或政治集团的“鲜卑”作对比,体现的是对和士开社会地位,而非族类身份的藐视;更重要的是,即便是政治权力争夺最大程度上塑造了族群边界,其分界也不可能不考虑血统与文化上的区别。和士开汉化程度不高,胡人特征明显,其家族也并非世代高官,远未达到令六镇鲜卑贵族将其归为“汉儿”政敌的地步。 因而,笔者推测,斛律光之所以称和士开为“一汉”,仅是一种单纯的贬低之意。问题是和士开当时身为宰相,怎能和“贱夫”相提并论?窃以为如若是侮辱性称谓,则其使用并不一定要与被称呼者合理对应。况且和士开为人奸佞,早为鲜卑上层人士深恶痛绝,视之为小人。因而此处使用的“汉”不宜过度解读。 3、韩凤其人 《北齐书》卷五十《恩倖转·韩凤传》载: 凤于权要之中,尤嫉人士……每朝士谘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辄詈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13] 苏航在其文中点评道:“韩凤对“汉儿”的歧视毫不掩饰,代表了当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的风气。”,而这种“汉儿歧视”实际上是“一种在政治资源分配上设置族类身份边界的做法”[14]。参考韩凤六镇鲜卑的身份,此言大概不差。不过笔者也发现,被韩凤骂作“狗汉”的对象实际是“人士”,即拥有较高汉文化水平的文官,其中应当也包括汉化较深的胡人。也就是说,在韩凤的辱骂之语中产生的族类边界,也有陈寅恪所言的文化上的因素。事实上,六镇鲜卑自己为作为打压对象的他者——“汉儿”所划定的边界,实际上掺杂着政治与文化上的考量。如果结合前文和士开的案例,则会发现血统之分也并非全然消失。因而,这种族类边界的划分标准应当是多元的。苏航文虽指出了这种多元性,但似乎并不认为,对于任意一次“汉”的族群边界的确定,多种不同的因素具有同时存在的可能性,因而其讨论仍希望为史料中每一次“汉”的称呼找到唯一的划分指标。 4、高氏君臣的启示 《北齐书》卷一《帝纪第一·神武上》载: 齐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欢,字贺六浑,渤海蓚人也。 同书卷二十四《杜弼传》载: 显祖尝问弼云:“治国当用河人?”对曰:“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显祖以为此言讥我,内衔之。 同书卷五《废帝纪》载: 文宣每言太子似汉家性质,不似我。 同书卷二十一《高乾传》载: 高乾,字乾邕,渤海蓚人也。父翼……朝廷以翼山东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七《梁纪十三》武帝大同三年载高乾弟高昂事: 明日,贵与敖曹坐,外白治河役夫多溺死,贵曰:“一钱汉,随之死!”敖曹怒,拔刀斫贵。 同书同卷载: 时鲜卑共轻华人,唯惮高敖曹;欢号令将士,常鲜卑语,敖曹在列,则为之华言。 高乾、高昂兄弟是高欢、高洋父子的臣子,根据正史记载二人都出自渤海高氏,似乎是同族,但二者的民族认同却截然相反,而且都表现出了对于民族身份的敏感,何也?察高乾之父高翼,是被朝廷认可的,当时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山东汉人豪族,其家族自然不会否认自己高贵的出身。而高欢、高洋等皇族虽自称出于此门,但实际已充分“胡化”[15],之所以依然自称出于渤海高氏,还是歆羡汉人士族的社会与历史地位。但不管是其自己还是时人,绝不会有人视其为“汉”。不过即便如此,高欢依然被敌人宇文泰称之为“汉儿”[16]。很明显,这里是宇文泰利用高欢自称的身世对其贬低之语,既不能代表高欢真实的族类身份,也不能说明时人对其族类的认识。由此可见,这一类的史料必须放在特定语境下思考,因而唐人刘知几以为这是宇文泰感自己汉化程度不逮高欢故之说不足取。 注释: [1]参陈述:《汉儿汉子说》,《社会科学战线》年第一期;贾敬颜:《“汉人”考》,《中国社会科学》年第6期。 [2]在笔者所参书目中,陈寅恪先生并未就该问题展开系统论述,不过其昭然纸上的观点长期以来多为治史者所认可,在学术史上有深刻意义,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另外,陈述先生的观点主要参照其《汉儿汉子说》一文;苏航先生的观点则参照其《“汉儿”歧视与“胡姓”赐与——论北朝的权利边界与族类边界》一文,载于《民族研究》年第1期。 [3]《北齐书》卷五十《恩倖·高阿那肱传》,中华书局点校本年版,第页。事亦见《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一《陈纪五》,中华书局点校本年版,第页,下文胡注亦出于此。 [4]引文见陈述:《汉儿汉子说》;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集》,三联书店年版,第-页,下引陈寅恪文同出此页。 [5]《北齐书》卷四十三《源彪传》,第页。 [6]苏航:《“汉儿”歧视与“胡姓”赐与——论北朝的权利边界与族类边界》。 [7]转引自桑原骘藏:《历史上所见的南北中国》,收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卷一)》,中华书局年版,第38页,下文引陆说同出此页。 [8]如《北齐书》卷三十《高德政传》载:“高德政尝言:‘宜用汉除鲜卑’,此即合死。”同书卷五《废帝纪》载:“文宣每言‘太子似汉家性质,不似我,欲废之。’”。同书卷二十一《高乾附弟昂传》载:“愿自领汉军,不烦更配。” [9]《世说新语》上卷上《言语第二》曰:“江左地促,不如中国。”即为证。 [10]《北齐书》卷十二《琅琊王俨传》,第页。 [11]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册(第四册)》,中国地图出版社年版,63-64页。 [12]《北齐书》卷五十《恩星·和士开传》,第页。 [13]《北齐书》卷五十《恩倖转·韩凤传》,第页。 [14]苏航:《“汉儿”歧视与“胡姓”赐与——论北朝的权利边界与族类边界》 [15]关于高欢的身世,研究者张金龙指出,高欢或的确为渤海高氏之后。不过其直系祖先因罪徙怀朔镇,受北族社会环境影响大,加之母系血统几乎全为鲜卑基因,在高欢之时,就民族性而言,已是彻头彻尾的鲜卑人。见张金龙:《高欢家世族属真伪考辨》,《文史哲》年第1期。 [16][唐]刘知几:《史通》,《中国史学要籍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刘丰源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ingxianglia.com/tsyxl/2229.html
- 上一篇文章: ldquo江西省最具影响力十大景区
- 下一篇文章: 领导影响力的九大指标管理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