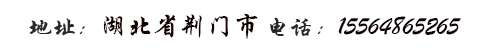聚焦集合影响力那些年成功的集合影响力案例
|
点击上方蓝字订阅我们中美印农村学前教育论坛将于年5月12日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举行,此次论坛我们邀请了许多在学前教育领域有丰富经验的国际机构的负责人,他们将与我们分享美国在农村学前教育领域的相关经验以及美国机构如何通过集合影响力实现规模化,在此之前我们先为大家带来了几个美国集合影响力的成功案例。通过这几个案例,我们可以更加了解成功实现集合影响力的五项条件。 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要求广泛的跨部门的协作 然而社会部门却依旧坚持单个组织的独自干预文:约翰·卡尼亚,马克·R·克莱曼美国公共教育的规模和复杂性使得拟议中的改革推迟了数十年。在承认他们的努力效果不佳之后,诸如Annenberg基金、福特基金会、皮尤慈善信托基金等主要的基金会都已经放弃了进一步的努力。这个全球曾经的领跑者——二战后有最高的高中毕业率——在24个工业化国家现在排行18,每年有超过万初中生辍学。无数教师、行政人员和非营利组织的奋发努力,数十亿美元的公益投入,可能带来了一些单个学校和课堂的重要进步,实际上并未获得系统广泛的进展。集合影响力案例Strive的案例与这些令人气馁的实事相反,一个明显例外出现在辛辛那提。Strive,这个KnowledgeWorks的非营利组织分部在大辛辛那提和北肯塔基致力于联合地方领袖,努力应对学生的学业危机,而且提高了教学效果。在三大公共学区,Strive的伙伴们提高了学生数十个领域的成绩。尽管遭遇不景气和预算削减,53项成绩指标中的34项表现出了积极的趋势,包括高中毕业率、四年级的阅读和数学成绩以及准备好上幼儿园的学前儿童数。为什么这么多的努力都失败了,而Strive却取得了进步。这是因为社区的核心领袖群体决心放下他们个人的日常工作,采取了一种提高学生成绩的集体路径。 超过个地方组织的领袖,包括影响巨大的私人和企业基金会、城市政府官员、学区代表、8个大学和社区学院的校长、上百个教育非营利组织和倡导群体的执行主任。这些领袖们意识到如果教育连续体的其他所有部分不同时得到改进的话,只是抓住教育连续体中的一点,比如更好的课后学习项目并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单个的组织即使强大并富有创新精神,也无法独自实现这个目标。 于是,他们雄心勃勃的使命变成了协作改进年轻人的一生,从摇篮到职场。Strive不再创造新的教育计划或者说服捐赠者花更多的钱。相反,通过审慎的再造流程,Strive使整个教育社群焦距一套目标,用同样的方式去衡量。参与的组织根据活动的类型比如早期教育和课外辅导,被分为15个不同的“学生成功组群”。在过去的三年里,每一个组群每两周在教练和主持人的召集下开会2小时,开发共享的成绩指标,讨论他们的进展。更重要的是相互学习,调整他们的工作来相互支持。Strive,作为机构自身以及它协助去促进的过程,这些都是集合影响力的例子,这是一群来自各个部门的佼佼者围绕着一个共同的议题来解决一个特定的社会问题的承诺。协作在这里已经是老生常谈了。社会部门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合作,关系网络和其他类型的共同努力。但是集合影响力的本质是完全不同的。不同于大多数的协作,集合影响力的本质包括以下几点:一个集中式的基础框架,一个专门的员工,一个结构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一个共同的议题,被广泛分享的措施,不间断的交流,而且在所有参与者之间被不断加强的活动。虽然很少,其他成功的集合影响力的例子一般集中在那些需要几个不同的参与者来共同改变他们的行为,以期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的社会议题上,就像是教育问题一样。伊丽莎白河整顿方案年,MarjorieMayfieldJackson协助开发了伊丽莎白河整顿方案,目标是清理弗吉尼亚州东南部的伊丽莎白河,这条河在几十年内已经成为工业废弃物的倾倒地。项目吸引了超过名的利益相关方,包括弗吉尼亚州的切萨皮克、诺福克、朴次茅斯和弗吉尼亚海滩的市政管理部门,弗吉尼亚州环境质量部、美国环境保护局(EPA),美国海军,还有诸多当地企业、学校、社区团体、环境组织以及一些大学。这些力量共同组织起来开发了一套包含18个方面的恢复该流域的方案。15年之后,该流域超过0英亩的土地被保护下来或者恢复,污染物减少了2亿1千5百万磅,最严重的致癌物质的浓缩物减少了6倍,水质有了显著的提高。在河流完全恢复之前人们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但是已经有27种类型的鱼和贝类动物已经在恢复过的湿地中存活,而且白头鹰也回到了他们在岸边筑的巢之中。萨默维尔塑身计划或者我们来回想一下萨默维尔塑身计划(ShapeupSomerville),为了减少和预防麻萨诸塞州萨默维尔市在小学阶段的儿童的肥胖状况,整个城市都为此付出努力。该计划是由塔夫茨大学杰拉尔德?J和多萝?R?弗里德曼营养科学和政策学院的助理教授克里斯蒂娜?埃康纳姆斯发起、由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麻萨诸塞州蓝十字蓝盾公司、马萨诸塞湾和梅里马克山谷联合劝募会赞助。这个项目吸引了政府官员、学者、企业、非营利性组织和市民,大家集中在一起定义了健康的含义,并且讨论了什么练习可以减少体重的增加。学校同意提供更加健康的食物,教授营养课程,而且推广健身活动。如果当地的餐馆提供低脂肪、高营养的食物的话,可以获得一份证书。城市组建了一个农贸市场并且提供健康生活方式的激励措施,例如为城市职员提供打折的体育馆会员资格。甚至人行道也被重新修饰,十字路口被重新粉刷,目的是为了鼓励更多的孩子走路上学。年至年间,在统计的社区儿童的体脂指数有了显著的降低。改善种植可可豆的贫穷农民的生活甚至一些公司已经开始运用集合影响力的思维来解决社会问题。生产MM巧克力豆、士力架和德芙的巧克力的玛氏公司在科特迪瓦已经与一些公益机构、当地政府、甚至他们的直接竞争公司合作,改善了超过50万种植可可豆的贫穷农民的生活,科特迪瓦是玛氏主要的可可豆供应地之一。研究表明,更好的种植方法和改良过的种子能够使每公顷可可豆的产量增加三倍,从而会显著提高农民的收入,也就能保证玛氏公司持续的可可豆供应。为了达成上述目标,玛氏公司必须聚集各方的协作努力,比如科特迪瓦政府需要提供更多的农业推广人员,世界银行需要提供修路的资金,双边援助机构需要支持公益机构改善可可豆种植区的健康、教育和营养等问题。此外,玛氏公司需要与他的直接竞争公司合作来解决供应链之外的、竞争前的问题。这些不同的例子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大规模的社会变化不是来源于单个机构的孤立的运作,而是来源于更好的跨行业的协作。虽然关于这种理论有效性的证据仍然不足,但是以上的例子也证明在减轻我们所面临的大多数很严重和很复杂的社会问题时,如果公益机构、政府、公司和公众能够被一个共同的理念聚集起来,产生集合影响力,那么是能创造实质上的更大的进步的。集合影响力与孤立影响力集合影响力不常产生,不是因为不能实现,而是因为很少被大家尝试。投资者和公益机构经常忽视集合影响力的潜力,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将独立工作作为社会变化的首选方法。大多数资助方都面临着一个任务——从一堆申请人中遴选出几个资助对象,他们试图确认哪些机构在解决社会问题时贡献最多。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受助方在面对被选择时就需要彼此竞争,着重展示各自的活动是如何产生最大影响力的。资助方做出判断是基于受助机构的潜在影响力,尤其是受助机构独立于其他类似影响力的组织。当受助方被要求评估其工作影响力时,这种举措实际上是将机构的影响力与其他所有可变因素隔离出来。简而言之,我们将非营利部门这种最常见的操作方式称之为孤立影响力。这种方式受解决方案与获取的资助所左右,这种方式嵌入到了每一个机构,这种方式融合了一种期望——那些最有效的机构得以成长或可复制,使其影响力能更广泛地拓展。资助方努力找到一种最有效的干预手段,就好象存在一种可以治愈教育失败的方式,他们所要做的仅仅是发掘工作——类似于在实验室探索医疗方法那样。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近万非营利组织都在尝试创新独立路径解决主要社会问题。他们通常各自为战,那些可知的、对社会进步有重要作用的资源需求量就会呈几何级数增长。近来趋势强化了这种观点。对公益创投和社会企业家精神日益增长的兴趣使整个社会部门大受裨益,比如:众多绩效良好的非营利组织被筛选出来且成长迅速,还有个别极其优异的机构得到特别关照,脱颖而出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尽管这种方式占据主流,但鲜有证据表明在当今复杂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孤立的影响力能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没有哪个机构可以为任一社会问题单独承担责任,也没有哪个机构能提独自供治愈手段。在教育领域,即便是那些最受尊重的非营利组织——如哈勒姆儿童圈(HarlemChildren’sZone)、为美国而教(TeachforAmerica)、和知识就是力量项目(KnowledgeIsPowerProgram,KIPP),已经为成千上万的儿童花费了数十年的心血,也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值得世人称道,但在数以亿计的美国儿童中需要帮助的人数数倍于此。对单个组织创造的孤立影响的依赖,因非营利部门的自我隔绝而进一步加剧。社会问题是在政府和商业活动的相互作用中出现的,而不只是来自社会部门组织的行为。因此,复杂问题只能通过跨部门联合来解决,这要求非营利部门之外的力量加入。我们不是想要暗示,所有的社会问题都需要通过集合影响力的方式来解决。事实上,一些问题最好由单个组织解决。在我和罗恩?海菲兹为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冬季刊上撰写的《大胆去领导》一文中,描述了技术性问题和适应性问题之间的差异。一些社会问题是技术性的,它们定义明确,答案事先知道,一个或几个组织就足以解决问题。比如说创建大学奖学金、医院或者为食物银行安装库存控制。而适应性问题则是复杂的,答案未知,或者即使知道答案,也没有哪个单独的实体有足够的资源或权威带来必要的改变。比如改革公共教育、恢复湿地、提升社区健康,这些都是适应性问题。在这种时候,要想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需要所以利益相关方的学习,并通过改变自身行为创造解决方案。从孤立影响到集合影响力的转变,不仅仅是鼓励更多的合作或者公私伙伴关系的出现。它需要的是达成社会影响的系统性方法,重点在组织间的关系以及向共同目标迈进。它还需要创造一套新的非营利组织管理,拥有足够的技能和资源,可以组合并协调集体行动必要的各种特定元素,最终走向成功。集合影响力成功的五项条件我们的研究显示:集合影响力的行动想要取得成功通常需要满足五项条件,它们在一起产生合力才能创造伟大的成就,这分别是:一项共同的议题,共享的评估系统,互相补位的运作,持续有效的沟通以及中坚的支持性组织。共同议题集合影响力要求所有的参与者都可以用分享的视角来看待变革,这就要求他们既要对问题有基本的了解,又能通过协商、采用大家一致认可的方式解决问题。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周围的资助者和非营利组织,他们认为自己是在解决同一个的社会问题,但是很快你就会发现,他们通常所做的都不是一回事。每一个组织对问题和终极目标的定义都会有些微的差异。当这些组织在各自的项目上进行独立工作时,这些差异很容易被忽视,然而正是这些细小的差异使得他们的努力产生了裂痕,最终动摇了该领域影响力的整体根基。集合影响力要求我们讨论并解决这些差异。这并不是要求所有的参与者认同其他每一个参与者对问题的各方面的意见。实际上,集合影响力仍然会保留这些参与者所持的不同意见。然而,所有的参与者必须认同集合影响力项目作为一个整体所规划的主要目标。以伊丽莎白河计划为例,需要了解公司、政府、社会团体和当地市民的不同诉求、寻求共识,才能推出可操作性的跨部门行动。资助者在促进各类组织采取一致行动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Strive项目这个案例中,许多资助者所做的不是只提供上百条的计策和对非营利组织的资助,他们是主动的参与到了该项目的核心目标中。大辛辛那提地区基金会调整了其教育项目的目标,使它与Strive项目更相适应、在教育项目上应用了Strive的年度报告卡作为测量自身项目进展的手段。而每次当有组织申请杜克能源公司的资助时,杜克公司都会问:“你是属于(Strive)项目网络的么?甚至新的资助者,卡罗尔.安及小拉尔夫.海利/美国银行基金会也表达了他们对教育项目的兴趣,因为他们对辛辛那提地区的所有教育领袖都参与到Strive项目中,投身当地教育、创造影响的情况深受鼓舞。共享的评估体系开发一套共享的评估体系是集合影响力的基础。如果对于成功的衡量及报告方法没有共识,就谈不上对共同议程的共识。基于一套精选的指标,在社区层面及向所有参与组织持续地收集数据、评估结果,不仅保证了所有努力的方向一致,也能够使参与者责权透明,并从各自的成功失败中学习经验。使用同一套评估方法评估数以百计不同的机构,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最近的网络技术进步使绩效报告及产出评估的通用系统成为可能。这些系统提升了效率,降低了成本,并能改善数据收集的质量和可信度,通过让被资助者互相了解各自的绩效而提高有效性,还能记录整个领域的发展。例如Strive项目中的学前教育项目就同意以同样的标准衡量结果,采用统一的循证决策方式。每种活动需要不同的评价方式,但所有参与的组织在同类活动报告中使用同样的评估方法。纵观多个组织的结果,能使参与者发现其中的规律,找到解决办法,并迅速贯彻落实。学前教育项目发现,儿童在幼儿园之前的暑假会退步。通过在所有学前项目中同时开展一项创新的“夏之桥”活动——这种技术通常在中学中使用,他们在一年之内,将整个地区的幼儿园平均准备分数提高了10%。相辅相成的活动集合影响力取决于不同利益相关者团体一起工作,并非要求所有参与者做同样的事情,而是鼓励每个参与者承担其所擅长的具体活动,支持他人的行动并与之相协调。集体行动的力量并非来自参与者的数量或努力的一致性,而是通过相辅相成的行动计划,将差异化的行动加以协调。如果希望共同的努力取得成功,各利益相关方的努力就必须适应总体计划。社会问题的多种原因及其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是相互依存的。他们不能被孤立的组织之间不协调的行动解决。例如,在伊丽莎白河项目(theElizabethRiverProject)中,所有参与者同意18点的河岸恢复计划,但基于各自的特殊能力,在项目中扮演不同角色。一组机构提供基层支持和市民参与,另一组负责做同行审查及招募自愿减少污染的行业参与者,第三组协调和审核科学研究。Strive项目中的15个成功学生网络(SSNs)在教育的不同阶段承担不同的工作。Strive并不规定个参与组织应该以何种实践为目标。每个组织和网络可以制定自己的进程,与共同议程一致,并了解共享的成果评估。持续性交流在非营利性组织、企业和政府代理机构之间建立信任是一个非凡的挑战。参与者需要通过几年的时间里的有规律的会议,来建立对彼此(行为)的经验,从而认可和赞同他们基于同样的初衷而做出的不同努力。他们需要时间去观察,他们自己的利益被公平地对待,(组织)所做出的决定是基于客观的证据,而且是对问题的可能的最佳解决方案,而不是对某一组织比另一者更加有利。即使是建立共同词汇的过程也需要花费时间,而这对于发展共同的衡量体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所有我们研究过的协同效力的倡议会每个月或每两个星期组织一次CEO层面的必须本人出席的会议。(这些会议)不允许缺席,也不允许派级别较低的代表。其中大多数会由(组织)外部的促进者来推动,且会议会遵循一个有组织的议程。比如Strive网络公司,他们进行规律性的会议已经超过三年时间。而不同的会议之间也同样会产生交流。Strive公司需要使用网络工具,比如GoogleGroup,来保证交流在网络中进行。一开始的时候,许多组织领导者会出席,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参与能够为自己的组织争取到额外的资金支持,但他们很快发现这并非会议的目的。他们真正发现的是学习的收获,以及和与他们一样,对问题有着热情和深入了解的人一起解决这些困难。中坚的支持性机构创造并管理集合影响力需要一个单独的机构,而且该机构的成员需要掌握特定的技能,才能在集合影响力中发挥主干的作用。协调需要花费时间,而参与的组织都无法留出任何(人)来做这些工作。因而,最常出现的失败的原因便是,(参与者)期望在没有一个支持性机构协助的情况下实现合作。中坚的支持性机构需要一个参与集合影响力行动组织之外的专职人员,通过不间断的促进,技术和交流的支持,数据的收集和报告,以及对保证集合影响力正常运作所需要的大量运筹和管理细节的把控,来计划,管理和支持它。Strive将中坚的支持性机构初期人员安排的要求简化为三个:项目管理者,数据管理者和促进者。集合影响力还需要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流程,以保证初创组织做出有效的决策。在Strive的案例中,员工们和通用电气公司一起合作,使得通用电气公司用于持续性质量提升的六西格玛流程能够适用于社会部门。Strive的六西格玛流程包括训练,工具和每个SSN用来明确共同议程,共享衡量(标准)以及行动计划的资源,并且该流程由Strive的促进者进行引导。在最好的环境下,这些主干组织能够具体地体现适应性领导的原则:集中他人注意力并制造危机感的能力,向利益相关方施加压力但并不过度的技巧,将议题的困难点和机会都合理呈现的能力,以及调和利益相关方之间冲突的能力。资助集合影响力如要集合影响力成功,可观的财务投资必不可少。参与机构必须投入大量时间工作,开发和运行共享的衡量体系,中坚的支持性机构需要有人员牵头和支持持续不断的工作,这些都需要资金支持。即便像Strive这样成功的项目,也要为筹款而挣扎。资助方不愿意为基础设施付费,而更加倾向于短期的解决方案。集合影响力所需要的正相反,资助方必须支持长期的社会变革进程,即使之前没有找到任何具体的解决方案。他们必须让受助方自我掌舵,必须陪伴集合影响力经年累月,必须意识到社会改变不仅来自于单家机构的个别突破性进展,而更主要来自于整体系统随着时间推移的渐进式改变。资助方的角色定位需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不再是资助一家机构,而是要引领一场长期的社会变革。支持非营利组织的创新方案,或者为某家机构提供能力建设,都已不再足够。资助者必须帮助创立并维系聚合的过程、衡量报告体系以及社区领导力,从而让跨部门的联合得以发生并发展繁荣。这种转变,我们在“大胆领导”以及年秋天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发表的“催化式慈善”中都有所提及。在“大胆领导”一文中,我们建议,资助者应对自适应问题的最有力的角色应该是,集中精力北京专业的白癜风医院北京哪家白癜风医院最好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ingxianglia.com/yxlrw/681.html
- 上一篇文章: 优秀案例展播中建投信托构建人才体系
- 下一篇文章: 写在仲裁圈的开篇分享交汇与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