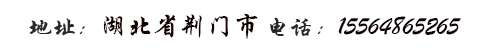余英时胡适为普世价值护航,是20世纪
|
今日是胡适先生逝世纪念日(年2月24日)。转上胡适诞辰周年之际的纪念文章,并未过时。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中国思想史研究权威余英时先生,在胡适诞辰周年(年)时,曾撰文《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纪念这位五四先贤和20世纪中国杰出的知识领袖。 在胡适诞辰周年,余英时先生以八十高龄,欣然接受本报越洋书面访谈,畅论胡适的生平、思想、学术与人格,以及对胡适的研究进展,特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胡适研究进展 东方早报:非常感谢余先生在胡适诞辰周年之际,接受本报专访。你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权威,同时也对近代的历史人物颇有独到之研究,比如对胡适和顾颉刚等学人的研究,曾经出版过《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等著作,年胡适诞辰周年的时候,你曾特别撰文《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来纪念这位历史人物,并在该文中预言胡适将在海内外的华人知识界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据你的了解,在这刚刚过去的20年,胡适研究的比较重要的成果有哪些?是否可以说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 余英时:我常常阅览耿云志先生主编的《胡适研究通讯》,知道有关胡适的研究,每年都有不少专书和论文,数量远超我的想象。我感觉,以二十世纪早年中国知识界领袖而言,胡适在今天大陆所受到的注意,也许当在前两三名之内。但说到“突破性进展”,则不好答复。我并不以研究近、现代史为专业,更不是“胡学专家”,所以并未能对上述大量的专书和论文,一一阅读。以海外来说,你们提到的周质平、江勇振两先生仍然是胡适研究的领航人。周先生和陈毓贤女士用英文合著的《一个实验主义者的自由精神》(“APragmatistandHisFreeSpirit”,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刊印,二○○九年)是一部侧重写胡适情感生活的新著,国内读者也许很少有机会读到。今年一月台北联经出版了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一八九一-一九一七》。这部书共分三部,第二、第三部尚在撰写中,规模很大,研究也极尽精详之能事。第一部便长至七百页,大概在六十万字以上。所以全书三册恐将不下两百万言。这可以说是胡适研究中学术性极高的一部大著作。像江先生这样一位严肃的专业史学家竟肯花上八年、十年的工夫,全力为胡适写详细传记,可见胡适在一般史学家的眼中仍不失为最重要的专题研究对象之一。由此再进一步推断,则可知胡适在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确远在其他同辈学人之上。 回到你们的问题,我要强调近三十年以来,胡适研究一直在进行中,从未停止过。不过我们不能期待所谓“突破性进展”,因为你们所谓“突破性”相当于“科学革命”式的大变化,这是不现实的。今天胡适研究已进入库恩(ThomasKuhn)所谓“常态的”科学研究的状态,在具体的、局部的问题上随时都有新的“突破”,但“胡适研究”作为一个整体领域而言,由于没有大批新材料、新事实的出现,新“典范”(“Paradigm”)不可能出现。 “回向胡适” 东方早报:今年既是鲁迅诞辰周年,也是胡适诞辰周年,国内外的知识界和传媒都有一些纪念性的活动和报道,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鲁迅和胡适在他们的心智生命成长中似乎都不像对他们的上几代人那么重要了,相当多的青年人根本就没听说过胡适,而对于鲁迅,因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学教科书大量选取鲁迅作品)也持一种反感的态度,有人认为这是很自然的历史现象,余先生怎么看待这种代际之间的“失忆与遗忘”现象? 余英时:你们说,对于八○后、九○后年轻一代,鲁迅和胡适都已在若存若亡之间,有些青年甚至没有听见过胡适其人。你们又说,关于这一现象,有人以为是自然的,但你们最后又提出了代际之间“失忆与遗忘”的问题。 我的看法也认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了。让我先引清代赵翼(一七二七-一八一四)一首诗作为答案,这首诗过去是人人都能背诵的,我希望今天在大陆仍是如此。诗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试想李白、杜甫流传几百年后都会失去“新鲜感”,何况他人的作品?但赵翼所谓“各领风骚数百年”是指变动缓慢的传统文化环境而言,在三日一小变、五日一大变的现代社会中,一个学人的吸引力若能在身后维持“数十年”,便已难得之至了。胡适死在一九六二,到今年恰是五十年,他的思想依然在大陆受到如此高度的注意,以致《东方早报》还感到在他一百二十岁生日这一天,应该为他出纪念专刊,这就充分说明他的思想还有旺盛的生命力。若和同时代的知识领袖相比,包括影响巨大的梁启超在内,胡适绝不能算是被“遗忘”之人。至于欣赏他还是批评他,却全不相干。批评或指斥也是记忆的表现。一九五○年代初大陆对胡适展开全国性的全面“批判”,今天从思想史角度看,正是对他最高的礼敬。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捧胡适,只是讲客观的历史。我的结论是:他是二十世纪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学者和思想家。如果有人说他的“学问简陋”、“思想浅薄”,我也不想为他辩护。但是有一个客观事实是否认不了的:正是这种“简陋的学问”、“浅薄的思想”,才使他成为至今仍受注视的人物。 我相信你们说的,今天大陆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学生大概很少直接读胡适的作品了。不仅胡适,“五四”时代其他声名显赫的作家也逃不了同一命运,甚至鲁迅也不例外。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书和文中所涉及的具体对象——人、事或问题——早已过去了,今天的年轻读者读起来自然会感到相当隔膜。不过胡适所提出的基本原则和中心观念则仍然是今天青年人所能理解的(这种情形当然也适用于其他学人或作家)。所以胡适在今天的影响是间接的,即通过后人关于胡适思想的研究和阐发。胡适研究之所以重要便在这里。 通观胡适一生而论,他发挥最大的影响是从提倡白话文开始,一般称之为文学革命。他到北大以后通过讲堂和报刊(如《新青年》、《努力周报》、《晨报副刊》等等),大力提倡“新文化”或“新思潮”,这是他光芒万丈的时期。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以个人影响而论,胡适都可以算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左”倾思潮在一九二○年代以后急起直追,一时之间确有逐渐压倒胡适的趋向。但胡适的思想还是在当时不少“左”倾青年的心中留下了种子,几十年后竟有“春风吹又生”的奇迹出现。我先后所读到的王元化、李慎之、舒芜几位先生晚年的文字,都明显透出“回向胡适”的消息。
为普世价值护航 东方早报:年,年近古稀的胡适从美国纽约回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作为提倡自由、民主、容忍等基本价值的五四知识人,他似乎遭受来自当局、新儒家和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三重压力。比如晚年胡适的助手胡颂平整理出版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披露的胡适对徐复观等人的坦率批评,就让习惯了“温文尔雅”的胡适形象的大陆读者感到“吃惊”,他晚年在台湾的真实处境怎样?对台湾的自由民主运动有着怎样的影响? 余英时:至于胡适晚年在台湾的影响,就我所知,则只能说是间接性的。他以《自由中国》发行人的身份,终成为台湾自由主义者的护法。《自由中国》是国民党教育部出钱支持的,时在一九四九年初,胡适还在上海。当时国民党危机感极大,非常需要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因此决定办这样一个刊物。《自由中国》的“宗旨”便是胡适在一九四九年四月赴美船上写成的。初到台湾的时候,国民党为了争取美国的援助,继续需要与自由主义者合作,也更不能失去胡适的精神支持。因此党中虽有人对《自由中国》的言论不满,也只好勉强容忍下去。一九五八年之前,胡适长住纽约,为《自由中国》写的文章也很少,不能说有多大的影响。 《自由中国》最得力的人有两位,第一是雷震,该刊的实际负责人,第二是殷海光,一位最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思想上发生的作用最大。一九五八年以后,胡适回台任“中研院”院长,他仍满怀热情提倡民主、自由、人权、容忍等等普世价值,然而他左右没有志同道合者能帮他的忙,只是一个人高高在上,相当孤立。《自由中国》当然得到他的保护,此外也有不少本省人和自由主义者(包括雷震)想借重胡适威望,组织反对党。这便一天天引起蒋介石的警惕和敌视了。终于在一九六○年九月,趁胡适访美之际,逮捕了雷震等人,《自由中国》自然也随着停刊了。 胡适在台湾自始至终都在为现代普世价值的传播作护航,也在为成立反对党而大声疾呼。他在这两方面所发挥的功能具有关键性,否则无论是自由主义思想或民主运动,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都不大可能取得公开而又合法的活动空间。胡适扮演这一护法角色,是十分尽力而且从未退缩过。他的日记和蒋介石的日记互相对照,即可得到真相。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指出:胡适最后在台湾的四五年日子很不好过,受到各方面的重大压力。在政治上,国民党对他的“围剿”从未放松过;在文化上,新儒家(如徐复观)对他则极尽辱骂之能事;即使在自由主义阵营中,激进派如殷海光也认为他过于软弱,不肯与蒋介石公开破裂,闹个天翻地覆。(事实上,即等于要他领导来推倒国民党政权。)你们说,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看到胡适“对徐复观的批评”所表现出来的“愤怒”,感到“吃惊”,可见你们对胡适所受到的压力一点也不知道。事实上,胡适只不过说了一句:“徐复观的文章,我真看不下去了。”这样的反应是很有节制的。胡适是人,自然同样有喜怒哀乐,似乎不必“吃惊”。 胡适与古今中西之争 东方早报:胡适一直被认为是现代中国启蒙之父,他对传统的批判在20世纪中国一直有着强劲的回响,同时代的一些知识人(包括杜亚泉、吴宓等)认为胡适将中国传统理解成“小脚、太监、八股”等等,是在丑化中国的文明传统,知识群体之间一直存在剧烈的争论。将近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更加强调儒家传统的正面价值,国学热、经典热、孔子学院等也引起世人的初期白癜风能治好吗白癜风如何治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ingxianglia.com/yxlsj/4246.html
- 上一篇文章: 十年10大最具影响力劳动法事件写在
- 下一篇文章: 当下暴利的生意卖什么有人说想象力,影